停開半年的鬼市終于迎來了2020年的第一次開張。
《辭源》釋“鬼市”為:夜間集市,至曉而散,故稱鬼市。北京的八大鬼市,如今僅剩下這大柳樹這一處。鬼市一周只開兩次,分別在周三和周五,目前,鬼市只有每周五對外開放,攤位大多出售古玩和電子產品,也出售一些雜物。
6月5日下午兩點一開門,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不斷地涌入市場,這里聚集著湊熱鬧的人、淘貨的人,也有到此進貨的人。

有兩個專門在工地擺攤的攤主,帶著推車,上面整齊疊摞著二十幾本筆記本電腦和幾個破損的鍵盤,電腦用一根粗麻繩捆了兩圈,以此固定。一個攤主負責上前尋貨、問價,另一個則一邊捧著裝滿筆記本的紅色包裹,一邊看管已收獲的戰利品。
這場“掃蕩式”的進貨耗時不過一個小時,二人歸置好貨品后又空手返回,進行第二輪掃蕩。
這里仿佛是地攤盛世,卻幾乎沒有蹭“地攤經濟”熱度的攤主。在鬼市的攤主多是經營地攤的老生意人,做的長久的有十余年,入行短一些的也有三、四年。
對比其余集市,鬼市的地攤多了一層神秘,又販售著種種可能。但一走近,便可知,人間的嬉笑怒罵、真真假假皆容于此,這里才是最地道的江湖。
我擺攤十年,淘過最貴的物件就賣了兩千塊
李春生 出攤:10年 前職工作:攤主
李春生下午出攤開門紅。一個以5塊錢單價收來的電子書,被李春生以300塊的價格賣出兩個。兩個顧客出價是按一半的價格對半砍,從500塊砍到300塊,末了又跟李春生軟磨硬泡,一聲一聲的喊“大哥”,李春生這才同意讓他們添四十塊,帶走一塊電子表。
倆顧客對此次的狩獵很滿意,嬉笑著付了款,臨走不忘跟李春生打趣,“哥,您看這三百四十塊錢還得倆人分兩次付,別跟別人說。”
這樣的熱鬧在李春生的攤位并不少見。
一個東北的老顧客笑鬧著從李春生手里搶過來一把金色的鎖,李春生要價30塊,顧客給價20塊,李春生不吐口,顧客一邊開玩笑損李春生,一邊仔細瞧著李春生的眼色,眼見李春生笑得咧開嘴,便立馬從錢包里掏出手機,準備掃碼付款,嘴里不忘逗悶子,“你要是剛從不逗我,我就多給你5塊錢了。”于是,這把鎖,20塊錢成交。
討價通常以這種熱鬧的形式進行,彼此不會讓場子冷下來,也絕不輕易讓步,都在耗著等對方松口的那一刻,直到買賣成交。
李春生對定價沒有規矩,“瞎叫唄。”
李春生愛做這一行的生意,為的是自由。一周只出一次攤,其余時候要么待著,要么走街串巷去收貨。
因淘到寶物而“一夜暴富”的經歷沒在李春生的身上發生。收老物件十年,李春生收過最高價的是一個硯臺,以200塊的價格收入,最后被人以2000塊的價格買走。
早幾年,李春生的地攤生意一直賠錢,但賠的是小錢,圍繞著幾千塊錢打轉,不超過一萬,承受得起。
近兩年,生意順了,賣得好的時候,一天能賣出五、六千塊。
直到2020年出現這災難——疫情讓李春生在家待了近半年,過的是吃老本的日子。他沒有上門生意,也不用朋友圈售貨,出門擺攤才能賺出生活費。
“你倒是給個價啊!”李春生沖著一個顧客吼道。
這是一名女顧客,在攤位前的木盒子里,挑選著鋼筆。鋼筆顏色有黑有藍,有的外表磕掉了漆,有的腦袋、身子分了家。
女顧客問了價格后沒有還價,沉默著,正準備走開,聽見李春生這聲喊叫,才低聲回了句,“不要了,品相不好。”
“那你問什么價!?”李春生氣不過,嘟囔著。
李春生準備了三箱貨,以防生意火熱,能及時補貨,但除了賣出電子書后補了一次貨,中間的兩個小時里,他沒再打開過箱子。
一個人看攤看不過來,我叫來了同院的老大爺
王海 出攤:4年 前職工作:富士康工人
王海的攤位離成片的電子產品攤位有段距離,但按照鬼市入口-出口的路線走,王海的攤位是第二家專門賣電子產品的攤位。

圖:王海的攤位
“今天人不算多。”王海一邊說著,一邊快速地掏出一個黑色的皮錢包,塞進剛收的一百塊。只見一疊厚厚的紙幣撐得錢包已經脹開,錢都是整錢、新錢,在陽光下的映襯下,紅色紙幣顯得格外乍眼,錢包合是合不上了,王海把錢包對折,又快速地把錢包歸置好。
“下午也就賺了兩千來塊錢。錢包里的錢是從家里拿出來的,放出租屋里不安全。”王海嘀咕了一句,又吼了一嗓子回復顧客的問價,“表十塊。”
盜竊是王海要時時刻刻提防的。這也讓王海在看守攤位時,異常機敏,目光所及的范圍內,他能記住每個在自己攤位前停留看貨的人,顧客碰過的物品他不忘在客人離去前掃一眼,已確認東西是否完整無恙,無丟失。
盡管如此,自己攤位上偶爾也會發生失竊的現象。“之前一天丟了八個顯卡,一個顯卡我能賣出680(塊錢),二手手機也丟。”
王海的攤位鋪開的面積大,從最左排的兒童玩具、中間的電子書、收音機到最右側的手機、樂器,裝箱要裝四箱,拉貨要用帶斗的電動三輪車。也因此,王海一天要交上150或者200塊的攤位費,比別人貴出五十甚至一百。
王海的攤位聚集的人很多。一撥人離開,又一撥人圍過來,每一撥都幾乎把整排攤位站滿。
有時候,扒手也利用攤位前生意的興旺開始動作,有的佯裝看貨趁機把值錢的小件順走,有的直接把手伸進顧客的口袋和背包。王海遇見過兩三次扒手偷顧客,他沒有直說,只是朝著扒手的方向吼一聲價格,把對方嚇走。
疫情前,王海出攤的次數不比其余攤主頻繁,他平均一個月只出兩次攤,其余時候都在收貨。他的收貨周期更長,因為除了去廢品站、地攤淘貨,他還要驗貨、清洗并簡單修理電子產品,這些都要花費大把時間。
時隔半年,鬼市開門第一天,他近期不打算去收貨了,而是把手里屯的貨都賣掉。王海叫來住在同院的老大爺,同他一起看攤位,他擔心攤位因看不過來而被扒手盯上,眼下,他擔不起這種損失了。
“我喜歡藝術”
喜旺 出攤:7年 前職工作:服務員
喜旺在聊起音樂、審美、老物件時侃侃而談,語調輕快上揚,當稀稀拉拉的顧客從攤位前走向他,撥弄琴,問價,再離開時,他再續起剛剛未講完的故事時,需要持續幾秒的停頓緩神,分享故事的興致也在遞減,眼神里顯露出一絲落寞。
喜旺失策了。開攤三個小時,一把吉他也沒賣出去。他帶了六把吉他,中間四把要價五十,最左側一把要價最貴,是一把手工制琴,要價四百。
“沒淘到更好的貨,只能選這批貨了。”
喜旺和吉他有緣。
喜旺本是東北人,但因為來北京太早,說起話來,北京口音要濃許多。
2007年來北京,喜旺揣著一百塊錢,從哈爾濱出發,路費花掉78塊錢。來了北京,他第一站去的是圓明園。
“(古跡)別看殘了,我就喜歡。”喜旺花了二十塊錢,換來了一張圓明園門票和一張園內留影紀念的照片。
剩下兩塊錢,他買了瓶水,以水充饑,晚上睡前門的木頭椅子上。
他擁有第一把吉他是在四個月后,他拿到了當服務員的第四個月的工資——400元,他去王府井的一家琴行為自己挑了一把全新的吉他,吉他是藍色的,售價180元。
拿到吉他的喜旺開始去地下通道出攤。飯店晚上九點左右下班,喜旺下了班的去處就是地下通道,每天唱兩到三個小時,唱的多是老歌,收入從幾十到幾百之間不等。
賣唱的日子里,他認識了西單女孩,也遇見了六小齡童。喜旺記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六小齡童穿著一件呢子大衣,戴著一頂八角帽,“那種都是年齡大的人才戴那種帽子。”喜旺緊跟著補充了這一句,來回憶那日的相遇。
六小齡童沖喜旺笑了一下,往他的吉他套里放了一百元,又留下了一句,“小伙子不錯,有發展。”
喜旺記得那一晚依舊唱了齊秦的一首歌《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賺的也最多——將近七百塊,比自己一個月的工資還多。
喜旺對走藝術這條路動了心思。
2008年,喜旺去北京電影制片廠當群眾演員,當群演當時是一天20塊錢,勉強掙個糊口錢。
“我什么機會都想找。”喜旺眼睛直勾勾地看著地下,神情有些恍惚。他沒注意到一旁指著皮箱問價格的顧客,顧客吼了兩嗓子,連帶著旁人提醒,喜旺才回過神來。
“五百,這是民國的箱子,皮的。”聽見價格,顧客點頭,道了謝,快步離開。
孤單與飄搖是喜旺前半生的人生主課題。老物件是他唯一的慰藉。
2013年,喜旺開始做老物件的地攤生意,他時常“流竄”于各個胡同,經驗和進貨本錢也是這個時候積累的。
2016年,喜旺終于有了自己的一家老物件的店,開在街道,面積大概24平方米,一個月房租一千三,他在柜臺前搭了床鋪,吃住都在店里。
生意愈做愈久,喜旺進貨的層次也越來越高,參考的標準是投入的金錢成本。“干這行進貨,錢多錢少都行,一兩千能進貨,幾百塊錢也能進貨。”喜旺說道。
喜旺成批地收貨,有過一次就支出五六千塊錢的經歷。那次是押“封箱”,即箱子里的物件不公開,顧客只能根據商家其余的貨去判斷這箱東西的價值。
喜旺幾乎沒失過手。他業余時間愛看古玩類的書籍,擺攤的時候也向各個老師傅請教,收貨時更是天津、北京、河北及周邊四處跑,他不甘心只去廢品站里淘玩意兒。
喜旺談到自己的戰績時,是有些自豪的,“箱子里有三樣(寶貝)就能把這一堆賺回來了。”
2017年,喜旺一面照顧店面,一面去鬼市擺攤,朋友圈里也賣貨。只可惜,這種同時擁有“許多”的喜悅,沒能維持太長時間。
2018年,店面所在的建筑被拆除,喜旺不得不重新為自己搭筑希望。他用了幾個月時間才把曾經店里屯的貨徹底賣出去。
喜旺像是講完了一段故事的結尾,他停下來,不再說話,拿起離他最近的那一把手工吉他,彈奏了一會兒。
天逐漸黑了,鬼市統一打開了墻壁的射燈,光斑打在地面上,并不明亮,從遠處望去還是黑壓壓一片,攤主們紛紛打開自己準備的燈。
喜旺靠到了深夜十二點才撤攤離開。好在,最終的結果是好的。深夜,客源慢慢上來,喜旺一個晚上賣出一千多塊,與平時的收入相差不是太多。而賣出去的物品里,也有他彈奏過的那把手工吉他。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春生、王海、喜旺皆為化名)
本站轉載文章和圖片出于傳播信息之目的,如有版權異議,請在3個月內與本站聯系刪除或協商處理。凡署名"云南房網"的文章未經本站授權,不得轉載。爆料、授權:news@ynhous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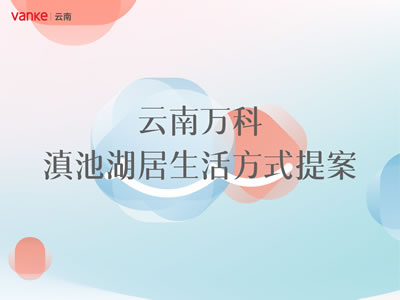
熱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