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邱與我差不多同時到加拿大,他聰明勤奮,運氣也好,留學時一路獎學金,畢業后也很快找到一份“白領”工作,并順利地拿到加拿大的移民紙。但他有一個“怪僻”:與其他中國大陸“白領”移民不同,他工作多年后,仍一直租房,就是不肯買房。
談起不買房的理由,老邱的解釋也很“怪”——他既非缺錢,亦非攢錢另作它用,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就是不想讓開發商和大銀行賺這個錢。”
在老邱看來,靠開發房地產賺錢的開發商和靠房屋抵押貸款賺錢的大銀行,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兩大支柱”。
噢,我忘了事先交待一句了:老邱常常自嘲,在中國時,他的經濟地位是個“貧下中知”,但思想傾向卻是個“右派”;在加拿大畢業工作后,他經濟地位升至“小資”,思想傾向卻轉變為“左派”。
我知道老邱心路變化的由來。
其實,大部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國的中國知識分子,雖然自命思想“右傾”,但卻是在住房公有制、單位低租分房的環境中長大的,而來到西方生活,他們感受到的最大的“文化震蕩”之一就是:再也沒有“單位分房”了,歐美租房固然很貴,但買房的錢更是一筆天價,對剛剛找到工作的工薪階層人士來說(不管“白領”還是“藍領”),用現金買房無異于“癡人說夢”,要想買房,唯一的選擇就是向銀行貸下巨款購房,然后再連本帶利,償還銀行貸款。
老邱曾對我說過:“在西方,租房是向房東租房,買房是向銀行租房。”他堅持不肯買房的邏輯是:雖然租房的租金也會占他日常花銷的很大一部分,但如果買房,他就不僅會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盤剝對象”,而且還會畢生成為大銀行的“還債奴隸”。
故鄉不再溫柔
西風東漸。老邱夢中的“溫柔故鄉”,如今也成了樓市開發商和大銀行“跑馬圈地”的賽場,而且這些年來中國城市新推出的樓盤,價格高得越來越離譜,一點兒也不亞于西方。新時代流行的一首“新民謠”這樣唱道:“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
中國房改所引致的社會新聞,雖然不像“死人送葬”、“大學生為籌學費而賣血賣身”等消息那樣聳人聽聞,但所引起的民眾不滿和輿論關注,卻絲毫也不亞于醫改和教改。那首“新民謠”不僅把房改與醫改和教改相提并論,而且把房改置于醫改和教改之前,似乎可以說明這一點;最近京城某房地產大亨一句“房產品牌就應該是具有暴利的”,不僅引起中國網民的憤怒聲討,而且也促使官方“新華網”在顯要位置推出火藥味十足的“叫囂房產暴利就是叫板和諧社會”的評論專輯,大概更能凸顯這一點。
然而,問題復雜就復雜在,房改不能簡單地等同于醫改和教改。你可以說醫療衛生和中小學教育是公共產品,大學教育是準公共產品,即使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沒有完全任其在市場的波浪中自沉自浮、自生自滅,但在市場經濟中,個人住宅卻是典型的私人產品,迄今為止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均實行住宅私有化和市場化,除非你想完全回到否認私有產權的計劃經濟時代,否則,你就不能一方面要求享有住宅房屋的私有產權,另一方面卻要求國家公款為你的私人產權“埋單”。
通常反對住房商品化、市場化觀點的理由之一,就是稱住房市場化有害于社會公正。但中國實施房改之前的單位分房制度,更難說是一種體現社會公正的制度安排:那時的住房制度,不僅有城鄉差別、地域差別、行業差別,就是同一單位中的分房,也是完全按照官階等級的差別分房。
例如,在中國首都北京,中央機關、北京市機關、區政府、事業單位、國營大企業,在分房的房源上,就有從富裕到緊缺逐級遞減的明顯差別,而北京有許多中小企業的職工,則基本上無法指望單位分房,更不用提那些根本沒有“單位”的個體工商人員了。
不過,住房又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既是一種生活必需品,又是一種代價不菲的生活必需品。貧寒之家可以不買珠寶、首飾,可以不買汽車、電腦,但卻不能沒有遮雨避寒的棲身之所;窮人無緣享受錦衣玉食,完全可以素裝簡衣、粗茶淡飯,但在建筑成本日增、卻又刻意強調都市美觀的中國城市中,即使是窮人,在住房上也沒有太多的節儉余地。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不論中西,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房產都日漸成為一種“把你腰包掏空”的高檔商品。在老邱看來,西方的房產不僅要把你目前的腰包掏空,而且還要把你今后許多年的腰包掏空。
政府如何干預?
那么,對這么一種代價不菲的生活必需品,是完全交由市場來擺布,還是完全交給國家來掌控,還是市場調節為主、國家干預為輔呢?
從已知的人類實踐來看,由國家完全調控、分配住房的嘗試無一成功:權力分房制不僅無法實現社會公正,而且造成了嚴重的住房短缺。房改前的中國住房狀況就是一例。
從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來看,即使是輔助性的國家直接干預,也常常以失敗而告終。
加拿大就是一個住房市場化為主、福利性住房補貼為輔的國家。在我曾經住過多年的多倫多市,市政府為了扶助買不起住房的低收入家庭,而提供一些廉租房,但政府財力有限,廉租房供不應求,申請者要排隊等待多年才能等到一次機會。由于廉租房比市場租價便宜許多,這種房租雙軌制還引致了許多舞弊事件:某些廉租房的租客把公寓中的一間或幾間按市場價轉租他人,當起了“二房東”。
英國的廉租房制度也出現了類似的弊端,撒切爾夫人擔任首相期間的保守黨政府為了革除這種弊端,曾作價把廉租房低價出售給租客,但即使是這種改革也引出另一種弊端:以遠遠低于市場價的金錢買下政府廉租房的前租客,不久后又以市場價轉售他人,狠狠地賺了一筆。無論中外,只要存在著雙軌制,就會有人從中牟利。
中國也有扶助低薪階層的“經濟適用房”,但一來供不應求,申請者為求一個房號全家接力排隊、甚至搭起帳篷通宵達旦排號的故事時有所聞,二來造假現象層出不窮,據說還有寶馬車車主住進“經濟適用房”的奇聞。
但完全聽任住房這種生活必需品在市場風浪中隨波逐流,也不可取。政府直接介入“球場”踢球,固然屬于角色混亂,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對于樓市無能為力,無事可做。政府可以通過控制土地審批、調整利率、征收物業稅等間接手段調節房價,也可通過降低開發商準入門檻、增加競爭、限制壟斷等方法來減少房地產業的暴利。競爭增加了,就會有人從事低端房地產市場的開發,以滿足低收入階層的住房需求。
房改在中國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公憤,原因很多:如官商勾結壟斷市場,開發商牟取不當暴利,海外熱錢炒高樓價,無人開發低端市場等,但也不能否認,由于中國在短短的時間內由單位廉租分房制迅速轉變為高房價的畸形市場化狀態,許多人難以接受種種確實不公正的現象,并因此歸咎于住房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市場化改革為不健全市場的弊病背了“黑鍋”。
房產的社會功能
離開加拿大來到英國后,我與老邱失去了聯系。前一段時間,老邱不知怎么搞到了我的電話號碼,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聊天過程中,我笑著問了一句:“你現在是不是還堅決不買房?”
出乎我意料,老邱很認真地說:“我已經買了一套房子。現在正考慮買第二套,作為一種投資吧。”
“老邱,你怎么也心甘情愿,當起了大銀行的‘還債奴隸’?”我忍不住這樣問他。
老邱也笑了:“你去英國后,我繼續租房,又堅持了一段時間。但后來我發現,如果我不想當銀行的奴隸,我就得當一輩子房東的奴隸。入鄉隨俗,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你要不想永遠當輸者,你就要按照他們的規則,與他們玩游戲,這樣你才有勝的可能。”
老邱停頓了一下,突然問我:“你知道維持西方社會穩定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一頭霧水:“不知道。”
“一個是精神因素:宗教,另一個是經濟因素:就是房產。”老邱一本正經地在電話中說,“中國古人就說過,無恒產者無恒心。過去,我常常感到奇怪,西方這么自由,這么多元,怎么沒有導致社會解體呢?后來我才知道,大概正是因為房產特別昂貴,大部分人都必須長期負債才能最終取得一個棲身之處,所以,這個相對自由、混亂的社會,才具有了某種穩定性。”
本站轉載文章和圖片出于傳播信息之目的,如有版權異議,請在3個月內與本站聯系刪除或協商處理。凡署名"云南房網"的文章未經本站授權,不得轉載。爆料、授權:news@ynhous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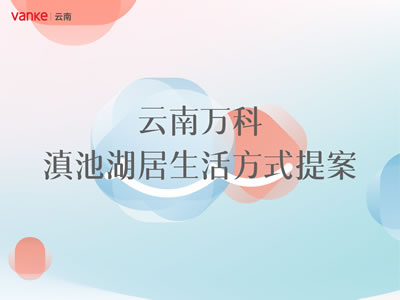
熱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