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包括北京在內的多個省市開始“拿英語開刀”了。他們或下調高考英語分數權重,或提出“小學三年級前不開設英語課”。
對于這些“改革新舉措”,贊賞者有之,憂慮者亦有之。
其實,你考或者不考,英語就在那里,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中國和中國人走向海外的必然選擇之一。
如果從1862年清政府創辦京師同文館教授英語至今,英語教育在中國已經走過了150余年。其間,英語地位的變遷和我們對英語態度的變化,勾勒出的不僅僅是一門語言在他鄉的經歷,還有我們自己走向世界的腳步和輪廓。
回顧英語在中國一個半世紀的起落沉浮,幾乎是中國近現代史風云變遷的一個縮影,而這門外語被搬上中國學校的課堂后,所引發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火花,更折射出國人心態的微妙變化。英語教學從何開始,因何興衰,緣何延續?翻開這門外語在中國150年的歷史,或許能為我們解答當下中國“英語難題”提供更全面豐富的視角。
若追溯古代中國最早的外國語學科,有證可考的是建于1289年元朝的“回回國子學”。后有明朝的“四夷館”,前清的“俄羅斯文館”。不過所教語種局限于波斯語、俄語等與中國接壤的少數幾個國家的語言。直到鴉片戰爭后,當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敲開清王朝的大門,英語才作為一門外語列入學校必修課程在全國范圍內盛行起來。
光緒帝的英文識字課本
今天的人們如想學習英語,最不缺乏的就是學習資料,更不用說鋪天蓋地宣傳的英語培訓機構。但在一個多世紀前,即便是大清帝國的皇帝要學洋文,想要一本英文入門課本都非易事。
戊戌變法前,清光緒帝為更多了解西方,決定學習英語,卻苦于找不到入門的教材。為此有大臣專門到匯文大學尋找英文識字書,恰好一位教授從美國為自己的女兒帶來一本英文識字課本,就送給了光緒。
坐落于崇文門的這所大學是美國基督教會在1870年創辦,是第一批在華傳播英語的教育機構之一。而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歷史最悠久的是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
經歷了閉關鎖國而被動挨打的屈辱后,清王朝認識到了解西方要從語言開始。正如恭親王奕欣在《奏設同文館》中所書:“以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識其文字,方不受人欺。”京師同文館也因此成為洋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1901年并入京師大學堂,即后來的北京大學。
1902年,清政府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規定全國的中小學堂外語課以英語為主,該章程于1903年正式實施,由此開啟了我國全國規模的外語課以英語為主的先河。一時間,翻譯西文、向西方學習之勢蔚然成風,英語教學開始初具規模。
全英文授課的教會學校
在最早期的教學機構里,就已經出現后被稱為“浸入式”的教學方法:部分教會學校全英語授課,學生從穿衣打扮到言行舉止全部模仿西方。而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背景下,重西學而輕國學之風更多是殖民主義的時代烙印所致。
如位于上海的圣約翰大學,在1918年把中文課全部改為選修,撤銷中文部,所有課程一律用英文教學。這使得該校在當時屬于西化程度最高的教會大學。曾在此就讀的林語堂回憶說:那時圣約翰大學是公認學英文最好的地方。但他也坦言,這所學校過分偏重西學使得自己忽略了中文。他在自傳中如此感嘆:“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約書亞將軍的號角,我都知道,我卻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淚沖倒了一段萬里長城。而我身為大學畢業生,還算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慚愧。”
《英語對中國的歷史性影響》一書的作者牛道生指出,彼時的英語教育更多強調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而較少觸及通過英語這門工具向西方傳達中國的文化的作用。但是教會學校的英語教育在中國的近代發展史中具有兩重性。它們在將西方殖民主義文化帶進中國的同時,也把西方的一些現代文明成果和先進科學技術一起帶進了中國,為長期接受封建傳統教育的中國人打開了一個借以瞭望西方文明的窗口。
救國運動的重要工具
為更快學習西方科學技術,19世紀下半葉中國出現了第一批“公派留學生”。1854年,早在清政府派遣30名幼童赴美留學之前,26歲的廣東青年容閎就以優異的成績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作為中國近代提出“教育救國”主張的第一人,他為后繼的中國留學生樹立了榜樣。
同樣為后人所沿襲的,或許還有清政府下令在小學開始教授英語的教育方針。
1902年,清政府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規定全國的中小學堂外語課以英語為主。兩年后,又頒布了《奏定學堂章程》,其中指出:“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勤學洋文。今日時勢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歷、游學無不窒礙。”這也成為中國學校普遍開設英語科的起點。
上世紀20年代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到來,中國教育界出現了學習西方教育的熱潮。1923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布的《新學制課程綱要》中規定從中學開始開設英語課,這也被視為中國教育界力圖與國際教育趨勢接軌的嘗試。
教育專家熊丙奇認為,過去150多年間中國不同的歷史時期,國人對待英語的態度不同和當時的歷史形態有關系。如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很多大學采取的是全英文授課,國外的教材剛出版就可以直接拿到國內教學,目的是希望快速學習西方技術,改變中國積弱積貧的情況。因此那時的英語教材和英文課程,對于中國的人才培養和科技進步起到了很大作用。也正是在那個時代,盡管國家面臨貧困和戰爭,但也出現了西南聯大這樣的學校,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政治英語的時代特色
在許多老一輩國人的印象中,他們熟知的第一外語并非英語,而是俄語。與他們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回憶一樣,外語學習也一度被賦予鮮明的政治特色。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強調向前蘇聯學習,英語受到排斥,大部分中學只開設俄語,這導致的直接后果是英語人才緊缺,俄語人才過剩。
1956年,周總理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指出:“為了實現向科學進軍的計劃,我們必須為發展科學研究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必須擴大外國語的教學,必須擴大外國重要書籍的翻譯工作。”根據周總理的指示,1956年起逐年擴大英、德、法等語種的招生規模。1956年底,全國23所學校設有英語專業,學生總數為2500人。第二年起,初中開始恢復外語學科,并提出除了俄語外,擴大英語和其他語種的教學。
1964年頒布的《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提出,“在學校教育中確定英語為第一外語,大力調整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開設外語課的語種比例”。這是首次明確英語在學校教育中“第一外語”的地位。到1966年,全國高等院校開設英語專業的學校達74所。
但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使包括英語在內的教育系統遭到破壞。政治英語和語錄一并被印上教科書。如翻開教材,第一課就是“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萬歲”。
“全民英語”和“聾啞英語”的糾結
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中國重新回到世界舞臺,對外交流大門被打開,英語才迎來了在中國的“黃金時期”。1981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國內興起了出國熱潮,其標志就是托福熱。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廣播公司制作的《FollowMe》(《跟我學》)于1982年在中國開播后,掀起第一波學英語的狂潮。有媒體做過統計,《跟我學》全國收視人群達到1000萬,與當時的電視機持有量基本持平。在那個影視作品貧乏的年代,洋溢著英倫風情的《跟我學》甚至成為了一檔文化娛樂節目。
步入20世紀90年代,人們學習英語的手段和方式有了更多選擇,民間培訓機構急速升溫,各種英語學習法如“逆向式英語”、“四輪學習法”、“雙向式英語”等層出不窮,“新東方”的俞敏洪和“瘋狂英語”的李陽一度成為英語學習的偶像。
然而對于“體制內”英語教學而言,新的問題出現了。應試教育的主導下的“全民英語”受到不少詬病。調查顯示,高校中有70%的教師對大學英語教學不滿意,而最讓他們不滿意的則是大學生們普遍的“聾啞英語”現象。
熊丙奇認為,過去30年來我國雖然重視英語,但是也出現了雙面的效果:一方面英語是改革開放的需要,作為培養國際化人才,外向型人才的工具,重視英語教育確實促進了國家的開放。然而同時英語也被當作了一種選拔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工具。
英語助漢語走出國門
反對全民英語的另一個理由中,是英語的“過火”影響到了漢語的普及,降低了中國文化的安全。
對于這種觀點,北京語言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寧一中并不贊同,他認為當下英語和漢語并非此消彼長的關系,學習本民族優秀文化和掌握外語技能本身不存在矛盾。關鍵在于根據社會的實際需求去考慮培養學生,提高質量。
事實上,當經濟飛速發展的中國已擺脫一個多世紀前的積弱積貧,英語在這個國度的角色也在悄然變化。申奧成功后,北京在2002年全面啟動了“百萬市民學外語”活動。同樣,上海為迎接世博會的到來,也掀起了全體市民學習英語的熱潮。
牛道生認為,如果說出國熱、考研熱帶動的英語學習過于功利,那么奧運和世博期間群眾性的學習英語熱情并沒有太多功利色彩,更多的是自豪感的體現,很多人提高英語能力,只為能在盛會上一顯五千年歷史大國的風范。
與此同時,伴隨著全球升溫的“漢語熱”,中國教育部于2004年創辦的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國落地開花,而在向全球推廣漢語和中國文化的過程中,英語正是作為一門重要的輔助教學語言。
同樣,在被網絡連接更加緊密的世界,漢語也正在逐漸影響著英語,“dama”(大媽)、“jiayou”(加油)等中文拼音不斷成為英文單詞,英語借鑒吸收的漢語詞匯已呈越來越多之勢。這些無不反映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正逐漸加強。(國際先驅導報謝來陳娟)
(云南房網為《云觀察》唯一授權發布網站,未經允許不得轉載轉帖,否則后果自負!)
本站轉載文章和圖片出于傳播信息之目的,如有版權異議,請在3個月內與本站聯系刪除或協商處理。凡署名"云南房網"的文章未經本站授權,不得轉載。爆料、授權:news@ynhous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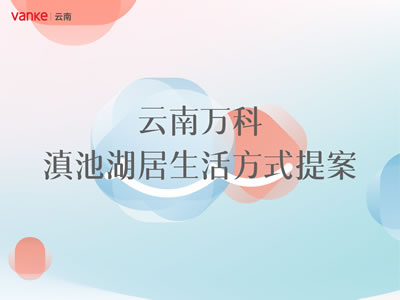
熱門評論